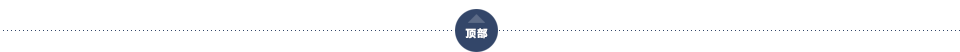今年1月至9月底,一共有上千名滞留在希腊的难民被顺利地 重新安置到多个其他欧盟国家,其中大多为叙利亚难民。这与数年前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的高峰时期,欧洲强烈的排外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得到安置的人数与需求相比仍然相去甚远,但这是欧洲在分担接收难民的责任方面迈出的可喜一步。这个消息令鲍里斯·切希尔科夫(Boris Cheshirkov)尤其感到欣慰。5年前,切希尔科夫是联合国难民署驻保加利亚的发言人,他对难民表达的支持让他在自己的祖国遭受了残酷的 “言语暴力”。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明在她的播客《夜不能寐》中采访了切希尔科夫。请听联合国新闻黄莉玲的报道。
2011年3月,叙利亚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演变为内战,迄今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9年多,同时也从内战演变为有多个外国势力直接参与的复杂战争。9年来,共有560万叙利亚人逃到国外,寻求庇护。
土耳其是叙利亚的北方邻国,很多人逃到土耳其,继而通过土耳其位于地中海东部的海岸乘船前往希腊,或者选择陆路,进入保加利亚,最终目的都是前往象征着“安宁与幸福”的西欧。
2013年夏秋之交,上万名叙利亚难民抵达了保加利亚。那时,切希尔科夫正在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驻保加利亚的发言人。
切希尔科夫:“那是八月下旬,我在黑海度假。我接到了保加利亚新闻社的电话。他们问我:您能确认有500人刚抵达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之间的陆地边界吗?” 的确有500人到了边界地区,大多数是叙利亚家庭。我们开车去了边境,看到的一切真是令人震惊。这群人待在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处小设施前的围栏里,那里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洗漱用品,连哺乳期的婴儿也没有护理用品,可以说没有任何支持结构。一天之内来这么多人已经压力很大了,第二天,又来了300多,到周末,已经有数千人。在9月份和10月份,有上万抵达,使接收系统完全不堪重负,保加利亚政府对此毫无准备。难民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住,被扔进了那些根本没有被改建过的废弃了几十年的军营。他们只是被锁在栏杆后面,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在刚开始的几天,只有红十字会给他们发个袋子,里面装着一瓶水、一罐豆子和一些金枪鱼。这就是他们好几天能得到的一切。情况太糟糕了。接着第一场雨来了。人们住在泥泞的田野里。然后,军方提供了适合夏天的军用帐篷,但这种帐篷不适合即将到来的冬天。”
作为难民署的发言人,切希尔科夫的工作顿时变得更加繁忙,每天都要开记者会,日夜回答来自数十个媒体的询问。
切希尔科夫:“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政治层面,反弹都是非同寻常的。人们说,不,我们不能接待这些人,他们会改变我们社会的本质,他们的人数会超过我们。这驱使难民署参与辩论,让我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明显。那意味着我开始每天出现在镜头前,或者参加早间节目。当时,每个人都变得完全失去了理性。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努力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接收难民会产生负面反应。我感到非常惊讶。在我看来,当人们逃离战争并来到我们的国家时,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这是常识,黑白分明,你必须帮助这些人。想在边界阻止他们,建造围栏,是毫无意义的。保加利亚的民间社会还不是很强大,现在仍然是这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难民署是当时唯一支持难民的声音。其他所有人,无论持什么信条或政治立场,都反对难民。”
一天半夜,熟睡中的切希尔科夫接到一个电话,询问有关边境地带难民被枪杀的事件。他迅速通过实地工作人员了解到,一些阿富汗人进入保加利亚后遭到边境人员的阻拦,在发生争执的过程中,一名边境警卫开枪警告,不幸子弹反弹,击中了一名阿富汗人的脖子,导致他当场死亡。
切希尔科夫:“实际上,这是欧洲难民危机中第一次有人在边境被枪杀。因此,我代表难民署说了一句话,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话是正确的。我说,我们对在土耳其和保加利亚边界保加利亚一侧一名寻求庇护的阿富汗人的死亡深表遗憾;我们对这一事件深感震惊;我们呼吁当局进行透明和迅速的调查;寻求庇护不是犯罪,这是一项基本人权。我对法新社、路透社和独立报都是这么说的。”
切希尔科夫那天上午7点安排了参加一个早间节目,本来谈论的是有关难民融入的问题。但走进电视演播室后,他发现,显然只能谈一个话题——就是这名阿富汗人的死亡。然后,他开始接到公共广播电台的电话,要求采访,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切希尔科夫:“最初,我认为这是针对难民署的,但很快,我发现是针对我的,是极右翼的人发动的一场运动,但是很快就渗入了主流。最初有数百人,但随后有数千人在社交媒体上说,替阿富汗人说话的那个人是谁?我们的边防部队需要进行保卫;他是叛徒;他是个拿薪水的叛徒;他不是保加利亚人,他是反保加利亚的人;他必须交出护照,他不是保加利亚公民。然后政治家门立刻开始谈论这件事……”
一位与权贵关系甚密的颇受欢迎的历史学家甚至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取消切希尔科夫的公民身份。同时,作为难民署的发言人,切希尔科夫的手机号码是公开的,他开始接到许多谩骂和威胁电话,还有类似内容的数百个电子邮件和脸书信息。
切希尔科夫:“我很清楚地记得最初有一个电话来自加拿大。我没想到会是保加利亚人打的。电话那头的人用保加利亚语说,你真不要脸;但是你也会死;而且我要寄给边防部队一支手枪和装满子弹的弹夹,好让他亲手杀死你。还有人说,现在我们要杀了你,我们正在组织,你不会在这个国家找到安全的地方。还有一些其他人只是妄想,他们会说:你会得癌症的,明天就会死;你全家都被诅咒;我们会找到你;我们会让你消失。还有人说,我很快就会往你脸上破酸液。”
在第一线工作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往往面临各种形式的危险,有可能是动荡国家的武装冲突,有可能是贫民窟的帮派暴力,也有可能是一个路边的简易爆炸装置。但人们或许很难想象切希尔科夫所遭受的如此严重的言语暴力。
切希尔科夫:“我有点麻痹了,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我已经多少习惯了少量的仇恨邮件和互联网上的挑衅。这很普遍。我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是经过了如此精心地组织,并达到如此的程度。好像有人打开了开关按钮,突然有一千个人直接瞄准了你。那天晚上,我像通常那样坐电车回家,车上有人盯着我。我的房东也给我打电话,他很有礼貌地告诉我:你今天说的话不对,你不应该说这些话。我关了手机,取消了脸书帐户,删除了所有这些邮件。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包括我的父母。”
第二天,切希尔科夫开始收到难民署同事表达支持的邮件和信息。消息传到了难民署欧洲办事处、传到了总部。
切希尔科夫:“我没有感到害怕。我还不知道事情的程度。那个阿富汗人是星期四晚上死的,星期五发生了那一切。 星期天下午,我接到了难民署目前在日内瓦总部的发言人威廉·斯宾德勒(William Spindler)的电话,他那时负责欧洲事务,他在电话里说:你还好吗?我们都很担心。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我当时正坐在饭厅里,崩溃了……我非常感谢难民署的迅速反应。我得到了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支持,当时高级专员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当然他现在是秘书长。他写信给我说:您将得到我的全力支持和声援,不要因为做了正确的事而感到难过……”
难民署对切希尔科夫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并做出了新的安排。首先,为了不再暴露他,让他从事远离媒体的工作;然后,将他调到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的莱斯博斯岛(Lesbos)。
有同事开玩笑地说,难民署就是这样,“让你刚离龙潭,立刻就入虎穴”。
的确,莱斯博斯岛离土耳其很近,每天抵达的叙利亚难民比保加利亚多得多。
切希尔科夫:“我到达莱斯博斯岛的那天是直到今天为止希腊海域最严重的沉船事故发生后几天。我是坐早晨的第一个航班去的。随着飞机驶近,我开始看到了岛屿的轮廓有一个橙色的光环。我们飞得更近了,我才看清楚那实际上是救生衣上的荧光在阳光下显现的颜色。我已经被告知这里的情况非常困难,但是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到了岸边,我看不到沙子或岩石,救生背心和废弃的船像地毯一样盖住了沙滩。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抵达。仅在2015年10月一个月里,就有13万5000人抵达。这个地方离土耳其只有几公里,人们凌晨四、五点出发,船一艘接一艘地行驶过来,有时一天达到两百艘,每艘船上可容纳大约50人。第二天,又是同样。有时天气很好,人们到了,他们很高兴。但是,有时在恶劣的天气和汹涌的大海中,人们晕头转向,踏上岸时人就散了架,而我们赶紧跑过去帮助他们。”
在莱斯博斯岛上工作的那段时间,一个叙利亚小女孩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切希尔科夫的记忆中。
切希尔科夫:“这小女孩可能最多只有10岁。她和家人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当我们帮助他们下船时,她只是站着不动,凝视着茫茫大海,身上穿着紫色上衣和搭配得很好的裙子,翻领上有一朵蓝色的布花。 她站在那儿,那是我见过的最空虚的凝视,唯一的动作是她的下巴在发抖。显然她的体温过低。我试图给她披上一条毯子,但是毯子不停地从她肩膀上滑落下来,我最后不得不用毯子把她牢牢地裹起来。他们都被海水浸透了。每个人都是这样。整个冬天,每天都有很多船到达,每艘船上至少有50个人,有时船不比普通的餐桌大多少,但却有88个人在上面,人们就像沙丁鱼一样叠在一起。在公海上经过三、五个小时,他们的腿麻木了,海浪从四面八方飞溅,所以几乎在每条船上都有体温过低的人。”
数年来,希腊一直不断地接收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难民,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德国和瑞典等国接收。莱斯博斯岛的莫里亚难民和移民接待中心人满为患,今年9月初发生了大火。这一事件再次暴露了局势的严重性,但这与其说是希腊的问题,不如说是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
切希尔科夫:“莱斯博斯岛是一个大岛,有9万人口。有成千上万的人专门帮助难民,当地人日复一日地在岸上给难民送茶喝,送毛毯,帮助人们渡过难关,把他们从水里拉出来,有时人还活着,有时已经没气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人们感到很沮丧,他们希望自己的岛屿回归原来的样子。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是他们仍然在提供帮助,他们仍然相信必须帮助难民。”
切希尔科夫在岛上工作了8个月,后来被调到难民署位于希腊首都雅典的办公室。
尽管在保加利亚遭遇的言语暴力已经过去很久,而且他也不相信会有人因为他为难民仗义执言而真地来杀害他。但那场“辩论”引发的思考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荡。
切希尔科夫:“我们都害怕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之后同很多与我亲近的人交谈,包括朋友、家人、亲戚,他们无意伤害我,但都不同意我和我所代表的难民署的立场。只有当他们遇到一个受到影响的人时,或者遇到一个像努尔(Nur)这样的人时,他们才会理解。努尔不得不把双手捂在他八岁儿子的耳朵上,因为孩子的母亲在隔壁的房间里遭到侵犯。当他们看到我们所谈论的完全是些普通人时,这些人是老师、工程师、学生、面包师、农民,他们除了过正常的生活以外从来不奢求其他任何东西,他们的孩子成绩不错,也许他们得到了加薪,也许今年的收成更好……当人们了解我们是在谈论这些普通人时候,就开始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加开放,并且不应容忍仇外心理。在21世纪,不应该存在这种‘我们、他们’的言论。‘我们、他们’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我有幸结识的一些来自叙利亚的学者,来自阿富汗的艺术家、诗人。我将永远没有机会在我居住的大多数地方见到这些人。”
黄莉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